忽然,女人伸手抱住安妮,说道“无论如何,我很喜欢你。”突如其来的拥抱虽有些粗鲁,却让安妮感到温暖。
女人像母亲一般拥抱安妮,又似乎有些丧气似的垂下胳膊,回到洗衣机旁边,“吮吮,现在,所有男人都想要,我做,至少没得病,你还好吗?”
安妮的脸“唰”的红了。
“好了,好了,宝贝儿,那是你的私事,我理解„„我姓腾,你可以叫我滕太太,你叫什么?””
“安妮。”
“可爱的中国姑娘,这么快有了美国名字,你很快就是全太太了。”
安妮张张嘴,想说什么,又止住了。
腾太太接着说,“年前,吉里就说他马上有妻子了。以前,他都要花钱找女人的。”
安妮听不下去,厌恶地想堵上耳朵,腾太太看出些端倪,走过来把手搭在在安妮的肩膀,“面对现实吧。”眼前的中年妇人,交谈的方式直截了当到令人难以接受,但一句暖人心的话语,便让安妮喜欢上了她。
洗衣店的门被推开了,一位气质高贵的中国女人朝柜台走来,阿甘包里塞满衣服。“嘘,”腾太太的食指竖在嘴边,“是沈夫人。”
只见沈夫人把包放在柜台,用普通话说,“干洗衣服。”
安妮在学校学过普通话,她带着广东腔用普通话问,“姓名、电话?”
“沈。”接下来,沈夫人说出一串靠近唐人街,俄国山郊区的地址,她居高临下地盯着安妮,安妮连忙拿起柜台上的钢笔,在便签纸上记录,然后从阿甘包里掏出一件件衣服,分别贴上标签。
沈夫人认真地看安妮写汉字。“从前,我在北京学得很不错,可惜现在退步了,你记账该用算盘。”沈夫人接过收据,踩着轻盈的华尔兹步走出店门。
“她对你刮目相看了。”滕太太说。
“为什么?”安妮问。
“你懂普通话。”
“我只懂一点,讲得不好。”
“别谦虚了,我了解她,如果你不懂普通话,她的眼神会像盯住一个卑贱的南方乡巴佬一样,叹一口气,然后换广东话跟你讲,显出贵族屈尊纡贵地讲乡下人的语言。对了,你会打算盘?在唐人街,这是旅游观光的重要表演。俄国山夫人,哈哈,太棒了。吮吮,你很性感,以后可以跟你丈夫玩这个游戏。”
“滕太太„„”安妮乞求道。
“好了好了,我冷静一下,大笑伤心脏。呃,这些衣服各自的价格,你清楚吗?”
安妮摇摇头。
“我来教你。”滕太太走近柜台,给沈夫人留下的每件衣服的标签写下价格,然后把干洗的价格和不同名目的衣服列了份清单。
“吉里该给过你。”
“是。”安妮心说。
说话的功夫,一个海军短外套,烟囱帽装扮的的高个白种男人“呼啦”一声推开门,大步流星地走到洗衣篮跟前,肩上的水手袋麻利地被甩进篮子。他走到柜台前,在便签纸上写出名字,掏出20美元搁在柜台上,便转身离去。
安妮很惊讶,泉尚洗衣店在唐人街中心,竟然还有白人客人光顾。
“他叫亚历克斯·伊凡诺夫,住在不远的北滩,爸爸是哥萨克人。”安妮好奇地听着,“亚历克斯和我侄子都做过码头装卸工。这些衣服可以洗了,洗干净后像这样折叠起来。”
“我要走了,”滕太太把自己洗净的衣服扔进烘干机,对安妮说,“你学得很快。”
安妮学着腾太太的样子,把亚历克斯水手袋的衣服一股脑儿抖进洗衣篮。衣服满是油渍,安妮转到柜台后面端出屯着的几盒洗衣粉。
“都是油污,要多洒些洗衣粉。”滕太太对安妮说。
半小时以后,滕太太离开了洗衣店,安妮不舍得快哭出来了,朋友,朋友,多想有个朋友。
那一晚躺在床上,安妮感到一只湿冷的手摸向她的身体,然后罩住她的乳房。安妮的皮肤绷得紧紧的,她眯着眼,却察觉不到什么。全吉里是不是想过,这个女人简直像麻袋一样没有知觉?吉里的舌头探进安妮嘴里,安妮知道有一根东西进入身体内,幸好没有快感,为了尽快摆脱全吉里,安妮从吉里身子下面挪到床尾,刺激吉里的睾丸,成功,吉里到了高潮。安妮小心地把吉里推下自己的身体,她轻手轻脚地,生怕吉里忽然翻脸,如同一只被猴妈妈遗弃的猴子那样暴怒。安妮连忙亲吻吉里的手背,心里幻想着吻的是林超的手。
今晚相比头一次,始终差强人意。
次日清晨,安妮独自待在洗衣房里,情绪才慢慢舒缓。
好在日子一天天过去,比安妮想象的快得多。
5
1849年夏,中国船停靠在旧金山巴特里街码头。船上载着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淘金者。那时,淘金者广受关注,却也备受嘲讽。淘金时代的人无暇逛酒吧和帐篷妓院玩乐,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寻找金矿。
在金矿区的问题上,众人产生了分歧。一拨儿人听说这边的方位有金子,而另一拨人相信朝那个方向才能挖到金子。于是,其余的淘金者便分成两派,分头跟随着踏上了淘金之路。全尚也是其中一员,同行的有三个老乡。他们起初只是给前往奥伯恩峡谷的淘金户做饭、洗衣服,但一路上历经险阻,自己竟也变成了淘金的矿工。很幸运,全尚他们真淘到不少金子。中国人得到了金子,这让反华情绪在淘金的队伍里盛行起来。一天夜里,全尚和同伴的黄金被偷了大半。全尚才赶忙带着埋在地下所剩不多的小块黄金返回了旧金山。比起被偷的,剩余的这些算不上财富,仅是娶妻、开洗衣店,倒也绰绰有余。后来的日子,淘金矿工发财,赌徒发财,调酒师发财,连妓女都发了财,可全尚苦心经营的泉尚洗衣店却一直不温不火,无缘于发财。
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雇佣中国人的时候,全尚认准这是人生的第二次机遇。但修铁路酬劳低,全尚很难攒下积蓄。幸好妻子打理着洗衣店。越洲铁路修好以后,全尚总算存下一点私房钱,汇给妻子和儿女。1906年初,全尚去世,他的家人就一直住在一所危房,直到1906年四月爆发了地震和火灾。
全旺生父亲的气。当初父亲全尚把积蓄都兑成少得可怜的金币,藏在地窖的保险箱里。“应该存进银行。想想利息。”全旺不断提醒父亲。可是当全旺在厚厚的废墟中挖出保险箱的刹那,他默默地感激父亲的先见之明。全旺欣喜地启开保险箱,难道记错了?竟然比印象中少了许多。难道是父亲赌博输了钱,亦或是有别的女人?全旺猜忌着。无论如何,先开家洗衣店,汇一点钱到中国,娶妻生子也足够。
全吉里,全尚的重孙子,也是如今泉尚洗衣店和房产的主人。
倘若吉里卖掉祖辈的房产,他一夜之间会成为富翁,但他又不得不重新买一套或者租一套,花光积蓄变回穷光蛋。保养房屋的花销大,洗衣店的水费高。全吉里在太平洋汽车护理站做全职维修工,薪水不高,洗衣店就赚点小钱补贴家用,他使劲存钱,可是每当刚刚存下一笔积蓄,就赶上大开销,什么房顶维修,热水器更换,几笔算下来,吉里又身无分文,只得向银行贷款。
6
安妮成为全夫人已经一个月有余。婚礼在市政厅草草地举办,婚礼一结束,吉里直接去汽车护理站上班了,安妮回去洗衣店。当天晚上,吉里的房事技术还是生硬得很,几下就泄了,没有丝毫 长进。而两人的生活从这天起正式步入常规。
晚上十一点整,安妮送最后一位客人离开洗衣店,锁上门,走进储藏室。她一边拖地,一边哼唱着轻松的歌曲。安妮喜欢清洁洗衣店,眼睁睁地看它焕然一新。全吉里歪着头,靠在折叠桌边数钱,他挑出零钱,一边按计算器,一边塞进从银行带回来的纸筒里,安妮心想,简单的加法吉里还用计算器,倒不如让她来算,安妮明白了,在吉里心里,根本没有安妮在财务上的位置。
吉里忽然嚷起来,“不多,钱不多。”
安妮不想理他,店里有时生意好,有时不好,总体上说,自从安妮洗衣店来了以后,洗衣店的收入比从前翻了几番。安妮明白,主要原因是顾客们喜欢跟她聊天。
吉里凑到安妮面前,“不多,钱不多。”他拉开嗓门嚷着,安妮盯着吉里浮肿的脸,心想他又去喝酒了,脸肿的令人恶心。
“看,”吉里展开一份供客人在店里阅读的星岛日报,快速浏览着版面,其中有女服务员,厨师,女裁缝,杂货店伙计的职位招聘。忽然,吉里指着一个招聘广告说:“哎,妈咪王的香魂屋,招聘优雅按摩女。”安妮淡淡地望着吉里茫然的表情,他似乎没弄清这个职位的含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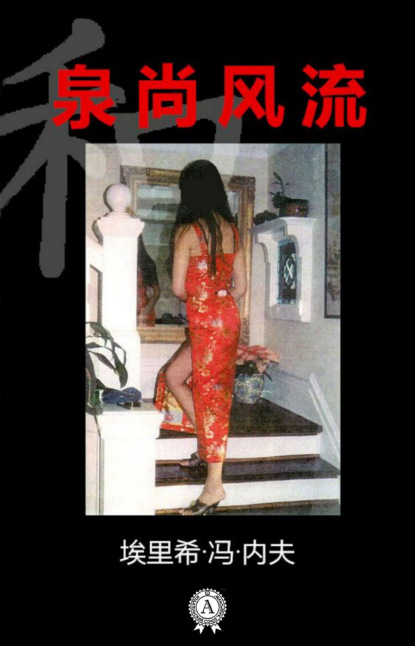




 Рейтинг:
0
Рейтинг:
0